

1990年11月18日
尼泊尔、印度、不丹之行已经圆满。当天,我们从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出发,飞抵泰国的曼谷机场。之后又花了半个小时转机,最终飞往香港国际机场。整个航程是六七个小时。
由于法王在印度和尼泊尔请了很多佛像,有些是自己的,有些是送给佛学院堪布们的礼物,坐飞机带不了太多,所以需要找人提前帮忙。后来,正好贝诺法王前往香港举办法会,坛城用品将通过航空托运,因此,我们就请他的随从将一些佛像、唐卡、檀木直接运到香港。其余的由我们自己携带。
我们有很多行李。每个人都请了一些佛像。我还帮几位堪布在印度请了几个大海螺,特别重。为了减少行李并帮助法王多拿一些东西,我把自己在尼泊尔请的很多佛像都送人了,只留下一尊小小的无垢光尊者像,以及那尊镶银的文殊菩萨像。因为尼泊尔不允许磁带出境,为了保存法王的讲课资料,我把磁带的黑色胶片取出来,将其缝在每个人的裙子里。
热巴医生喜欢印度布的僧衣,一口气买了好几件。为了减少托运的重量,他把所有衣服全套在了身上,一层一层的披单、一层一层的裙子,看起来特别滑稽。法王打趣他道:“你今天也太胖了吧。”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。
在尼泊尔过海关时,边检人员又找理由刁难。我们塞了一些钱,好不容易过去了。
抵达香港后,过海关也比较麻烦。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,我们是大陆护照,入境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,排队、填表、盖章都很费劲。用了四个小时才办好一切,然后乘车到达贝诺法王在香港的中心——香港密宗宁玛派白玉佛教中心。
该中心位于九龙柯士甸路,不是太大。大殿不到100平米,用于日常开法会、做会供等。此外还有一两间工作室,以及一间贝诺法王的房间。贝诺法王没有在中心住,法王就住他的房间,随行人员在大殿里打地铺。
1990年11月19日
我们把法王这次取的伏藏、唱的道歌,编辑成了一本簿薄的册子。听说香港的拍照技术特别好,顺便请法王在香港拍一张照片,加上那个册子,算是回佛学院后给僧众的礼物,法王也同意了。
我们去了香港比较著名的照相馆,并带上了白玉中心的法座。法王戴着在印度南卓林得到的莲花帽,安住于一种特殊的等持中,加持见闻、接触这张照片的人得到利益。照相馆的要求非常高,反反复复拍了很多次,最终效果令人满意。拍完照片后,我们仔细收好胶卷,到成都后冲洗了很多张。
在我的记忆中,法王有几张照片是特意安住在一种境界中拍的:
第一张是1984年法王在佛学院传授“四心滴”灌顶时,有人要给法王拍照,法王叮嘱他先别拍,自己要在大圆满中安住一会儿,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会有特殊的加持力,并希望将来得到它的人能发愿放生。那时,我还没有来佛学院。正是因为这张照片,我第一次认识了法王。

第二张是1987年在五台山的那罗延窟,法王开取伏藏“文殊大圆满”时拍的。

第三张是这次在香港拍的。

第四张是1993年法王在西方弘法时,在加拿大拍的。

后来,在成都、佛学院也拍过一些。但早年这几张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
法王每次拍这样有特殊加持的照片,都有放生的要求,有时候还会在照片的背面按上手印。我刚来佛学院时,若要得到有法王手印的照片,并没有规定放生数量。但后来要照片的人越来越多,只能规定每个手印要放一万个众生。依靠这种善巧方便,藏地和汉地的许多人纷纷放生,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。单单是这个功德,普通人几生几世也难以完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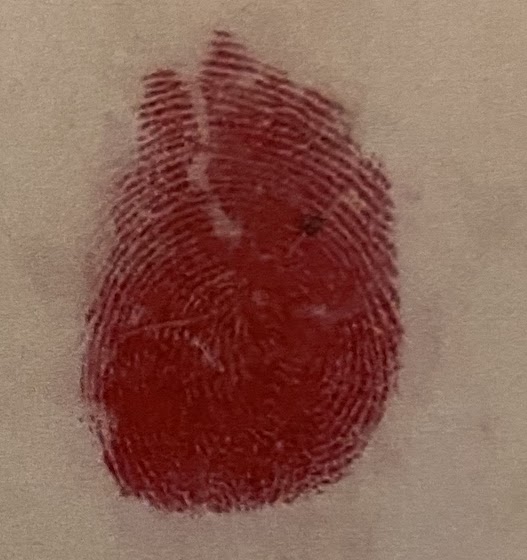
如今,按有法王手印的照片,仍保留在许多信徒的手中。对有信心的人来说,这是一份无上至宝。且不说法王本人示现的神奇事迹,单单是依靠这些照片,也发生过许多稀有、奇妙的故事。
1990年11月20日
当时,贝诺法王也在香港。他每天都来到白玉中心,和法王一起用餐,由不同的施主轮流供斋。白玉中心的住持经常在早上向法王报告:“今天,某某小姐请客。”那时,我对世间了解不多,以为“小姐”很年轻,结果到了下午,见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

在这几天里,法王参加了该中心的“三根本”会供法会,并为香港的佛教徒灌了顶,做了简单的佛法开示。我在印度时没办法翻译,到了香港,就可以给法王当中文翻译。但是,当时香港的语言与现在不太一样,我的语言他们听不懂,只好又找了一个懂香港话的人再次翻译。

在香港逗留期间,我看到每一次贝诺法王外出弘法,都会将所有供养汇给他在印度的道场以维持僧众的生活,非常有感触。印度的道场与藏地不同:藏地僧人的生活是家人供养,道场也受到信众的护持;在印度,当地人几乎不信佛教,信仰佛教的藏族人也条件不太好,因此,很少有人供养道场。上师们维护一个道场并不容易,所有费用必须自己想办法。许多高僧大德都很辛苦,他们经常去欧美、东南亚等国家传法,获得一点钱后,再用来修建寺院、塑造佛像、培养僧才,包括支付水电费。
当时,贝诺法王在香港、台湾和新加坡设立了佛教中心,所有的供养都用来维护道场,自己的生活很简单。他道场中的僧人主要来自藏地和不丹,没有生活来源,甚至僧人的衣服也都由上师来发。有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:“藏地是弟子供养上师。而你们这边,是上师供养弟子。”不过,这些僧人在学习上非常精进,无论是辩论、造论,还是相当不错。由于经历过磨难,许多人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。
在那个特殊的时代,贝诺法王为弘扬宁玛派教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特别是在培养僧才方面,贝诺法王、法王如意宝确实与众不同,对延续佛教的慧命功不可没。
当看到这些上师的发心,我深受感动,并发愿,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会随学他们的伟大行为。后来,在过去的30多年里,为了培养汉族僧才,我在传讲佛法、翻译法本、修建经堂、安排住宿、凑集生活费等方面,默默花了一些精力和心思,可以说是尽心尽力。即使在今天,法王已离世16年了,我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我希望将来很多人也能延续传承上师的传统,继续培养僧才、传递佛法、利益众生。
1990年11月21日
因为是第一次来香港,很多人说应该去海洋公园看看,所以我们安排了时间去那里。
当法王和我们第一次看到海底世界时,深深感到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。法王说:“由于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,这些众生转生为这样的身体,真是很可怜。”当导游在每一站介绍动物时,法王会默默为它们念经加持,有时还会大声持诵释迦牟尼佛的圣号。
之后,有人推荐我们坐过山车。其实,法王血压很高,按理说不能坐,但那些人也没有制止。法王和我坐在同一个车里,往上的时候比较舒服,突然下冲时,我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法王下来之后,显现上不停地呕吐,头痛。
然后,我们坐车去深圳海关办理入境手续,花了三个多小时。通过海关后,我们发现法王买的沉香小茶几少了一个。我回去找了很久,结果在边检人员办公室找到了它——他们组装了小茶几,将它放在自己屋里,上面还摆着一些水果。我和他们交涉了半天,好不容易才要回来。
在这次折腾之后,我最喜爱的念珠掉在那里了。念珠是木质的,有一颗珊瑚隔珠,我用了好几年,法王也加持过很多次,自我出国以来,就一直用它念文殊心咒,还在扬列雪念了10万遍金刚橛心咒。虽然茶几找回来了,但念珠丢了,回来后我伤心了半天。尽管也可能是前世欠他们的,今生必须给点东西来偿还,但茶几他们应该用得上,念珠肯定用不上。
然后,我们赶到广州机场,飞机晚点两三个小时。当法王在候机时,因为坐过山车一直头痛,非常难受,所以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。当时正在下雨,我给法王打伞,法王拒绝了,说这样淋着很舒服。我想为法王买一碗面条,没想到平时1元的面条,机场居然卖15元,我们吓坏了,第一次感受到机场的东西很贵。但还是买了,法王勉强吃了几口。
法王长时间坐在雨里。因为刚从印度那么热的地方回来,穿得很薄,我们担心法王着凉,又买了一条毛毯。法王披着毛毯,一直坐在大雨中……这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,我每次去广州机场都会想起。
飞机很晚才起飞,晚上12点多到达成都,飞行了2个多小时。
之前我在香港时,给色达县的人发了第二封电报,请他们转告佛学院:法王要回来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许多弟子下山前往成都迎接。因为通讯不发达,他们只知道法王返回的大致时间段,但不知道具体的日期,所以在成都等了好几天。
得知法王当天会到达,他们激动不已。那时,成都的机场比较破,很多地方都不规范,有些弟子通过找关系,前往下飞机的地方接法王。另一部分弟子求机场人员放他们进去,被拒绝后,他们看到旁边是铁丝网围栏,就硬闯了进去,机场人员也没拦住。结果,法王一下飞机,看到下面全部是弟子,每个人都捧着哈达,含泪等在那里。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,法王看到他们之后的第一个动作,就是将怀里的小狗拿出来,笑着问道:“这是我在印度得到的,它叫布廓。可不可爱?”
在广州机场,我们的一些行李被扣,因为超重。到达成都后,我正在想办法时,遇到了一位商人,他问我是否需要帮助。我谈到了这个情况,他连夜飞到广州,把东西带回来了。我记得,他夹着一个黑色的包,手里拿着一个“大哥大”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“大哥大”。
1990年11月22日
在成都休息一天。
法王外出时,每到一站,都会给随行人员开个小型会议,以交代相关事宜。当天的会议,算是一次总结性会议。
法王告诉所有人:“这次前往尼泊尔、印度、不丹的朝圣,非常顺利圆满。在回到佛学院之前,我打算在成都附近转一转。几年前我去五台山时,也顺路去了成都附近的有些圣地,但是南珠堪布、吾智喇嘛没有去过。这次出国他们非常辛苦,再加上汉地有些寺院一直邀请我去传法,所以这几天我有一点时间,想再去朝拜周围的寺院、圣地。这样的话,朝圣就更加圆满了。”
因此,我们安排了一个新的朝圣之旅。
1990年11月23日
在80多岁惟印老和尚的邀请下,法王去了他的寺院——成都大邑县白岩寺。
惟印老和尚是诺那活佛、贡嘎上师的弟子,后于101岁圆寂。白岩寺是一个修学藏传佛教的寺院,历史悠久,据说是东汉时期印度高僧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所建。这个寺院位于一座山上,没有通公路,所以法王去的时候,需要用人力轿抬上去。
到达白岩寺后,法王给寺内僧众和随行人员传授了“文殊大圆满”灌顶,并为当地人做了佛法开示。之后,惟印老和尚把该寺供养法王作为弘法道场。
去白岩寺传法,因为交通不便,需要坐车、换车,还要爬山,来回折腾花了一天时间,法王显得也比较累。但只要能让众生从佛法中受益,这些辛苦对法王来说再正常不过了。
1990年11月24日
应88岁清定上师的邀请,法王去了昭觉寺。昭觉寺是藏传佛教寺院,清定上师在汉地非常有名望,也是法王的好朋友和好弟子,他经常介绍自己的弟子去依止法王。
法王与清定上师进行了简短的佛法交流。之后,朝拜了寺庙里的佛像,并给僧人们一一摸顶加持。
当天闻名而来的信众特别多,法王用佛法与他们结上了善缘。
1990年11月25日
法王去了宝光寺,朝拜了寺内的佛塔、五百罗汉像。
1990年11月26日
上午,法王去了成都的文殊院。
之后,有一位近百岁的汉族老和尚,叫云登嘉措,他修学藏传佛教,再三祈请法王去他的小精舍。法王答应后,去待了一会儿,做了加持和简单开示。
1990年11月27 – 11月28日
法王参加了四川S委、省TZ部的几场会议。
他们要求我们提供出国期间的所有资料、行程、照片,并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汇报。同时,还询问了法王去尼泊尔、印度、不丹的一些事情。
1990年11月29日
朝拜了乐山大佛。但我们没有爬山,只是在河对岸发了愿。
抵达乐山市后,当地佛教协会迎请法王共进午餐。当天我们住在那里。
1990年11月30日
去了峨眉山。同行的,还有20多名从佛学院来接法王的弟子,在成都期间,他们一直随法王朝圣。
法王没有去山顶,只是朝拜了山腰的万年寺。那里有一尊高大的普贤菩萨像,还有迦叶佛的牙舍利。法王带大家念了《普贤行愿品》发愿。
1990年12月1日
南珠堪布、吾智喇嘛离开成都,返回印度。
法王启程回藏地,经过雅安、二郎山,很晚才到康定。
1990年12月2日–12月3日
在康定,参加了甘孜州ZJ局、TZ部的相关会议。
1990年12月4日
从康定出发,晚上到达道孚的绕果寺。当地的僧俗信众很多,法王给他们做了一些佛法开示。
1990年12月5日
从绕果寺出发,返回喇荣五明佛学院。一路上,从佛学院下来的弟子们在道孚、炉霍等地,一站一站地迎接法王。
到达佛学院后,以嘎多堪布为主的众弟子热泪盈眶——期待已久的法王终于回来了!
每当法王外出归来,都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。当时,佛学院只有一个甘多拉经堂。法王首先去了经堂,给僧众简单汇报了这六个月零三天的出行情况:自离开佛学院后,先去了成都、拉萨,再到尼泊尔、印度,去不丹,又返回印度、尼泊尔,后经过香港到成都,朝拜成都附近的圣地,今天顺利地回到佛学院。
尽管已是寒冬腊月,但弟子们看到了久违的法王,感觉温暖又回到了自己身边,激动之情无法言喻。
再次回到佛学院,我也像回到了家一样,特别开心。既然我没有留在印度,回来后就要为汉族四众弟子好好传法。当时我的中文不太好,翻译水平还不够,所以从香港带回来《大圆满前行》《藏密佛教史》的一些译本。直到汉语水平提高后,我自己才开始翻译法本,并不间断地讲经说法。
当时的汉僧,条件比较艰苦,没有法本,没有经堂,没有住房,我一直在努力改善他们的闻法条件,甚至亲自帮他们修建一些土坯房。后来,汉僧的数量日益增多,1991年评选出第一批堪布、堪母,法王亲自颁发了证书。
1990年12月6日
法王去了色达县。有关部门举行座谈会欢迎法王归来。在会议上,法王有点不高兴:“当我下山时,你们答应在我回来之前给佛学院供电,但现在还没有做到。”许多领导听后有些尴尬,立即答应安排人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当时已是天寒地冻,许多工程很难施工。特别是插入电线杆时,必须先烧牛粪以融化地面上的冰,然后才能将土挖出。虽然他们只安装了一部分电线杆,但过了段时间后,喇荣终于通上电了。
在过去的10年中,喇荣没有电。我来佛学院后的5年里,只能依靠煤油灯、酥油灯学习。第一天来电时,每个人都欢呼雀跃,感到在电灯下学习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
之后,佛学院又通了电话线。法王说,整个佛学院可以有三个座机:一个在法王的家中;另外两个,放在男众区和女众区。女众区的,在日雪堪母的家里。男众区的座机,也许法王去印度时对我各方面比较满意,说可以放在我家中。
我记得那是一个红色的座机。放在我家之后,我整天都提心吊胆,因为法王随时会打电话给我,让我通知一些事情,或是去找一些人。法王在电话中的声音,似乎比平时更威严。每当我拿起电话,法王都会习惯性地问:“啊咧,你在做什么?”我一听法王的声音就特别紧张,浑身发抖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1990年12月7日–12月9日
我请了几天假,回炉霍去看望父母。
父母是牧民,住在拉嘉山谷的帐篷里。在过去的六个月中,我们没有任何联系。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了,突然看到了我,非常惊讶,就像看到复活的人一样,母亲甚至高兴得泪流满面。
在我出国之前,我只是告诉他们去印度,并委婉地暗示这次时间可能有点长,但他们不知道我打算在印度待三年,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。
这次见到父母,我也很高兴,在家里住了两天。
1990年12月10日–12月11日
我去朵芒寺拜见了帝察活佛、德巴堪布,汇报了这次出行情况,并给他们带了一些加持品。帝察活佛很高兴地说:“我们朵芒寺的人和法王一起去了印度,这是寺院的荣耀。当你出国时,我们什么也没给,但你回来后,却没有忘记我们。”
我过去只是朵芒寺的小僧人,从那以后,他们对我寄予了期望。帝察活佛反复说:“现在,你在法王身边闻思修行,将来一定要多关照朵芒寺。我们这些老人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这么大的寺院,为这么多部落传法的重任,如今都在德巴堪布一个人肩上,将来你要多帮帮他。”我也答应了。因此,在这些上师离世后,我对朵芒寺尽心尽力直到今天,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当时,德巴堪布为朵芒佛学院的20多名僧人在讲中观。寺院的条件很差,大家辅导时没有教室,就坐在墙角的土堆旁边。但是,他们闻思非常精进,包括帝察活佛也在听小僧人的辅导。研讨期间如果有任何疑问,活佛说他不敢去找德巴堪布,让小僧人去请教一下。
实际上,帝察活佛是朵芒寺最大的住持,也是一位伟大的上师,1986年法王还请他用五个月时间给喇荣僧众传过《大藏经》的传承。但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,仍然在小僧人面前听法。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我遇到一些非常傲慢的活佛时,常常会想到他的举止。
1990年12月12日–12月25日
我回到了喇荣。在过去的几天中,法王将他这次所取的“项袋金刚橛”等伏藏,全部传授给了佛学院僧众。
法王见我回来了,说从国外买来的木制家具已从香港运到成都,我能不能去拿一下。我立即答应并动身下山。
由于这次不是跟法王一起,因此没有专车。诺尔巴堪布陪我从喇荣走到色达,等了一天也没有车去成都。第二天中午,终于找到了一辆邮车。我们跟许多信件一起挤在后车厢里,非常憋闷,再加上道路特别颠簸,晕车严重,不断呕吐。到八美时,吐得都快虚脱了,只好下车,改坐拖拉机。坐了一会儿后,发现了另一辆车,然后辗转到了康定。
我认识康定的一些老居士,他们帮我们买了去成都的大巴车票。抵达成都后,拿到了法王的家具,东西不多,大约一二十斤。回去时又转了几次车才到佛学院。前后总共花了十几天。不像现在,只需打个电话,一两天内快递就送上山来了。
看到印度的这些家具后,法王还是很高兴。尽管高僧大德断除了一切执着,但显现上也有自己需要的缘起物。对我来说,无论上师要什么、做什么,都不会以分别念判断它是否有必要。只要上师需要,就肯定有密意,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它做好。
1990年12月26日
回到佛学院后,法王把我叫过去说:“这次我们出行非常顺利,我对你还是很满意。你做事很勤快,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,包括整理文字等,都非常好。特别是在保密方面,很多事情能守口如瓶,什么该说、什么不该说,很有分寸。虽然我们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,但能守护秘密是重要原则。再过三年,我准备去美国、加拿大等西方国家,如果你愿意,我想带你一起去。但我不知道此行能否顺利,所以你不要对任何人讲,而且私下还要做一些准备,包括办理去美国的手续等。”我也答应了,然后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,其间非常低调且保密。直到去美国之前,包括签证在内的所有手续都已办完,法王才向僧众公开。
当时,慈诚罗珠堪布感到非常惊讶:“你们手续办完了我才知道,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?”我说:“法王要求保密,跟谁都不能说。“他说:“你保密太严了。”但他的心很宽广,不会斤斤计较。
法王去美国时,只带了我一个弟子。在那个年代,能去印度和美国是很不寻常的,尤其是与法王一起去,大家都非常羡慕。对我来说,一方面觉得特别荣幸,同时也感到压力巨大。由于邀请方的费用有限,因此陪同人员很少。不像去印度时,有人专门做饭、有人医疗护理,而去美国时,这些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,许多事情必须事先考虑,随时随地不敢松一口气。
由于法王带我去过一些国家,有人就说法王认定我是谁的转世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法王从来不会认定谁是活佛,这也不符合法王的性格。法王圆寂之前,只是在大众中说:“索达吉堪布在我的事业中从未破坏过缘起。将来,有些事情若与他商量,应该可以圆满成功,这对成办事业很有帮助。因为师徒之间的缘起非常重要。”我觉得这是法王对我的一种认可。除此之外没有说过什么。
1990年12月27日
我收到了雅绕寺的来信,他们敦促我尽快请购《麦彭仁波切全集》。正好我在师范读书时的同桌,就在德格印经院。我把钱寄给了他,让他帮忙请一套邮寄到佛学院,然后我再想办法转给雅绕寺。
我这次出行没有花很多钱,主要是因为贝诺法王的资助,以及一些人的供养。所以我回来之后,钱比较宽裕。我就拿出1400多元修了一间半的木头房子,这也是佛学院很早的绷壳房。直到今天,我仍然住在里面。
1990年12月28日之后
法王依次传讲了《上师心滴》的“前行修心七法讲义”“正行光明藏讲义”“直断本住讲义”。
此后,法王评选了63位堪布,并颁发了证书。这是喇荣五明佛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——以前我们只有“堪布”的称号,但没有正式证书。从那时起,佛学院也开始有了五部大论的分班。
之后,佛学院成立了一个理事会,分管教务、财务、后勤等部门。
之后,法王给僧众传授了“文殊静修大圆满”灌顶。
之后,法王传授了自己著作中的一些密法。
之后,法王说他将在佛学院建造一座万人大经堂(现为喇嘛大经堂)。经堂所在的位置,当初是一片很大的空地,周围有铁丝网拦着。法王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亲自去勘测地基,色尔坝的工人用绳子在测量,我们新成立的理事会成员也在场。
法王带大家念了“八吉祥”“大自在祈祷文”等。此时,在整个喇荣山谷的天空上,白色的祥云一条条发散出去,从西向东延伸。
法王很高兴地说:“我在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时,天上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祥云。看来,我们建造大经堂的缘起非常好!未来佛法会继续兴盛,僧团日益壮大,持教大德也会长久住世。我的寿命本来是66岁,但现在看来,可能就像诸大德授记的一样,寿命会得以延长,至少可以摆脱寿障。
我希望我们师徒暂时不要分离。大家都安心住在这里,守持清净戒律,以知足少欲的心精进闻思修行。如果能这样,未来你们一定能弘扬正法、利益有情。
尽管我的眼睛现在看不清文字,但我仍会尽最大的努力传授显密教法。尤其是密法的传讲,我相信,会给你们很多堪布带来利益。至少,我不会欺骗大家。
我们喇荣曾出现过十三位虹身成就者,是一个清净而神圣的地方,没有被破誓言的晦气所染污。今后,这里将继续涌现大成就者。即使我离开了世界,我相信喇荣教法将在一段时间内,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广泛地传播。那时,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喇荣和老父亲我……”
法王为未来做了一些授记。由此,正式拉开了弘法利生事业的帷幕…